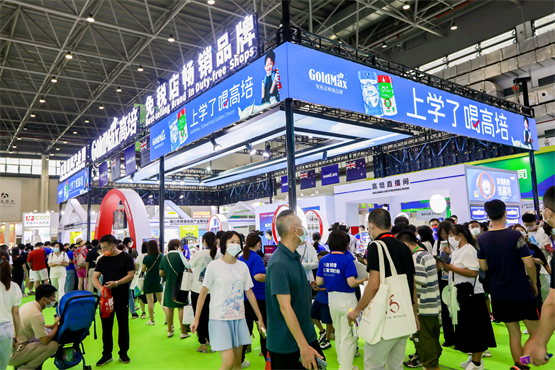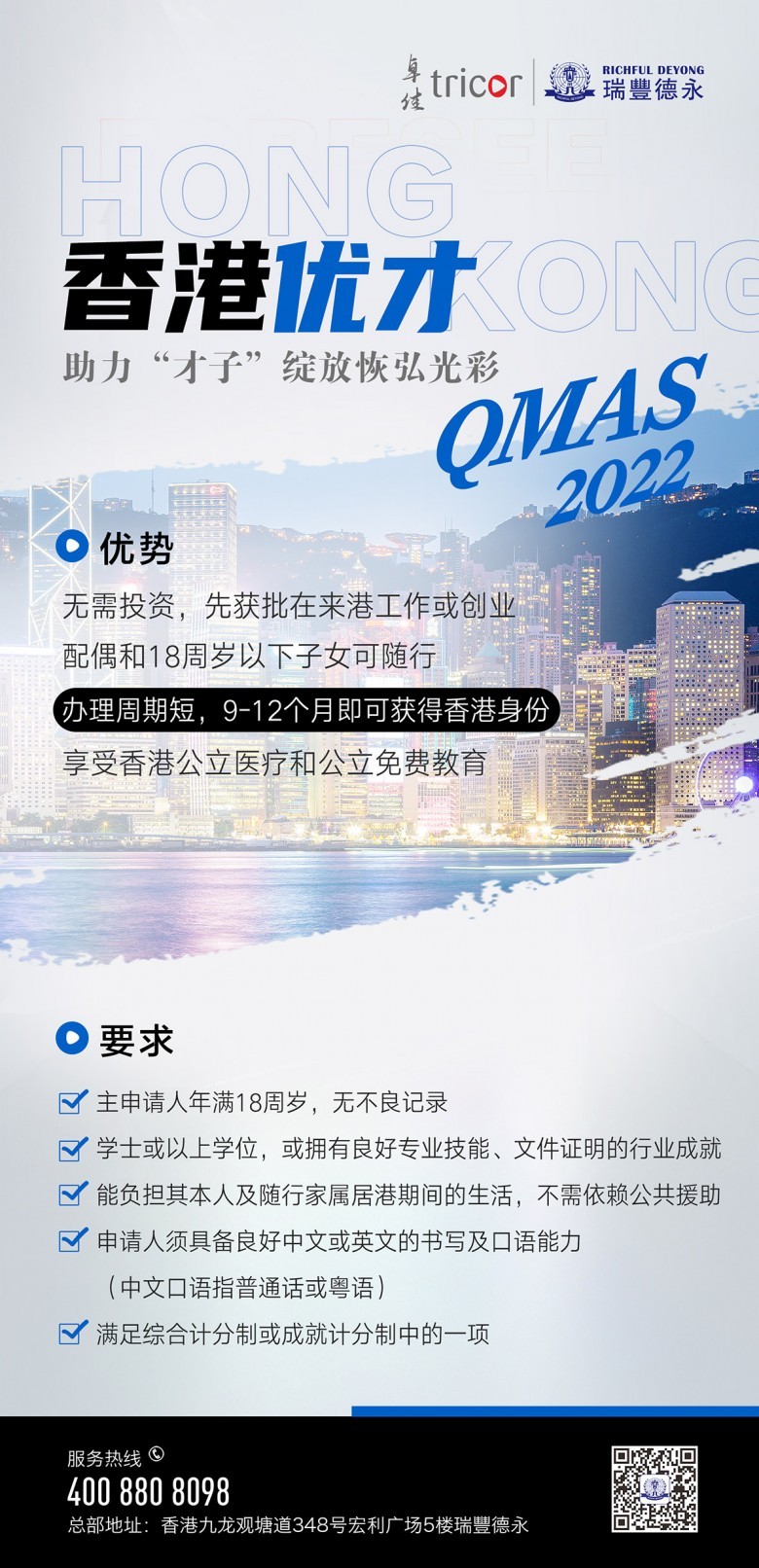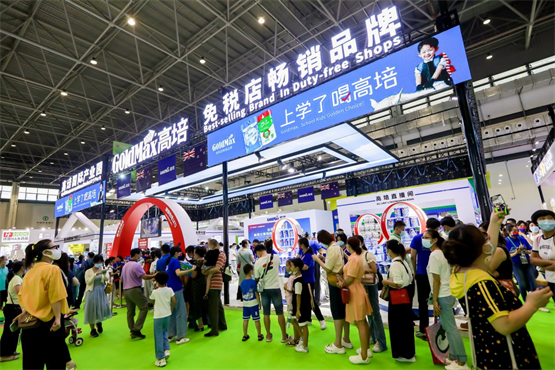20世紀初,在旅游基礎設施不盡完善、旅游環境“一言難盡”的年代里,長途旅行很大程度上是少數社會群體才有能力完成的壯舉,這是因為在旅途中充滿著未知數甚至艱險。甘肅是那個年代游歷西北的必經打卡之地,天南海北各路“驢友”的游記里紛紛留下了自己身在隴原、人在囧途的各種記載,讀來形象生動,折射出“中國西北游”早期拓荒者的若干歷史剪影。
南方人的熱炕體驗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古往今來,住宿乃旅程中頭等大事。對于今天的“驢友”而言,網上預訂住處是司空見慣的行前常規操作。而在當年,住店的可選擇余地甚小,旅甘人士特別是南方“驢友”雖然大多能夠入鄉隨俗、因陋就簡,但因生活習慣差異,對于在甘肅的住宿體驗尤其是對熱炕有著自己的獨特感受或點評。
1917年元旦之夜,湖南衡陽人謝彬(1887—1948,字蘭桂,號曉鐘,辛亥革命元老,集學者、教育家、經濟學家、旅行家于一身,年輕時走南闖北留過洋)進疆途中夜宿甘肅定西境內某小客棧,其在住宿方面頗為講究,選了條件最好的單間——其實就是一孔窯洞。剛住進定西窯洞時還很新鮮,回憶起自己1913年和1914年的元旦分別在日本箱根和東京度過,而今年元旦卻是在旅甘途中,謝彬不免唏噓感慨一番。然而謝彬的新年第一夜卻于輾轉反側中度過,原因無他,炕——實在是太熱了!據謝彬日記所載:“宿處為一窯洞,店伙燃馬糞於炕下,溫度過高,至不能睡,如受炮烙之刑。”
而對于在謝彬后腳赴甘的浙江蒼南人林競來說,熱炕卻并未給自己帶來多少溫暖,至少不會熱得夜不能寐。其在1919年1月16日日記里記載,“昨夜宿干塘,早醒視被面,沙土馬糞,厚積寸許,滿室昏迷,如墮霧中。蓋狂風扇揚,破窗而入,徹夜未休也。”同月18日日記記載,“昨夜宿紅水達拉拜(今景泰境內)大車店,夜來天氣驟冷,筆墨盡凍,作字甚難,乃以墨盒置熱水壺上,執筆一字一呵,方始作成。”同月22日,林氏抵蘭,入住蘭州西關集成客棧,終于進了省城,總算可以改善住宿條件,興奮之情溢于日記:“房屋雖卑陋,以視沿途小店,殆無異天堂矣。”隨著時代進步,20世紀三四十年代,蘭州及其他重要節點城市逐步擁有西式招待所或旅社,但熱炕記憶對于彼時“驢友”來說,仍然不失為體驗西北普通民眾生活的一種方式,正如林競所言:“天下事有其苦者,必有奇樂。旅行者之生活,毋乃類似。”
在此,還得提及當年的著名旅行達人孟述祖,作為南方人士,他在抗戰時期長期旅居甘肅,雖然亦曾有過睡熱炕的種種囧事,但并不妨礙其對于熱炕的“熱愛”,并專門著文一篇,題目就一個字:炕!(后收入《西北花絮》一書),言簡意賅地講述了甘肅熱炕的相關故事特別是熱炕在百姓生活中的不可替代地位,也算是為甘肅熱炕打了廣告。
路況惡劣,車在囧途
清末民初,旅甘人士出行基本上依賴騾(馬)車等畜力交通工具,旅途艱辛往往一言難盡。20世紀30年代以后,隨著西北地區公路網的逐步建成,汽車逐漸成為那些不差錢的旅行者們的首選代步方式。然而,囿于當年的車況特別是惡劣的路況,人在囧途通常也是車在囧途的同義詞。
1935年5月,西蘭公路通車。彼時國民黨元老邵元沖一行乘坐大小汽車六輛赴陜、甘、青、寧、蒙等省視察,算是開西北環線游之先河。據其秘書高良佐著《西北隨軺記》載,“邵委員西行以來最艱苦之一日”就在甘肅永登度過。當天究竟發生了什么令中央大員刻骨銘心?那是1935年5月21日,車隊白天自西寧出發趕往永登,深夜抵達永登城外莊浪河畔,“星月無光,夜色沉沉;急流湍激,澎湃而來。”司機打了半天喇叭,永登駐軍趕至,以手電筒指示涉水過河路線,不料汽車剛下水就陷入河中,“急流直逼車頂,衣物盡濕,其勢岌岌。”眾人見勢不妙,匆忙背負邵遠沖涉水上岸,其他隨員亦自行從車中游出登岸。至次日拂曉,“車幾盡沒水中,御車者呼救不已,繼以哭聲,眾復以馬渡出。”據《西北隨軺記》載,這幾位司機在此后河西走廊行程中,每遇河流,不分大小,均戰戰兢兢,可見莊浪河畔之夜留下的心理陰影面積之大。
美國人經常被稱為生活在汽車上的民族,但85年前的蘭州至肅州(今酒泉)汽車之旅,卻令當時應邀來甘勘探石油的美國地質學家馬文·韋勒印象深刻。1937年秋,馬文·韋勒一行分乘兩輛卡車(舊“萬國”牌和新“雪佛蘭”牌各一輛)自蘭州赴肅州,他在《戈壁駝隊》一書里以日記形式回憶了沿途的糟糕路況特別是層出不窮的車輛故障:9月9日下午,前往永登途中,舊“萬國”牌卡車因軸承箱過熱拋錨,傍晚修好上路,但又兩次陷入泥坑,全體乘客被迫推車;9月10日晨,因夜間氣溫低導致電瓶故障,舊“萬國”牌卡車無法發動,由“雪佛蘭”牽引,折騰一小時后才上路;9月14日晨,自涼州啟程,出城不到兩英里遭遇陷車,當天中午在永昌午餐時,一輛卡車的傳動裝置發生故障;9月15日上午,赴甘州途中,一輛卡車爆胎;9月17日下午,車隊在高臺附近陷入沙丘;9月19日晚抵達肅州,用馬文·韋勒的話說,終于可以感謝上帝讓他們結束了這段磨難,感覺自己的牙床都要顛簸松動了。
華家嶺上強人剪徑
出門旅行,安全第一,當年主要是防身。
1932年秋,上海《良友》雜志西北攝影團臨行前,曾計劃購置槍支防身,后據過來人點撥,西北地區響馬彪悍,騎射技藝高超,區區幾枚滬上“小開”,手里沒槍倒還罷了,若是手里有槍反而容易引起綠林好漢關注,搞不好還會搭上性命,于是被勸退,打消了買槍念頭。
但對于崇尚牛仔精神的美國人來說,不帶槍就在異國他鄉的田野上長途旅行,是難以想象的事情。美國地質學家馬文·韋勒和他的搭檔,乘坐郵輪抵達上海后,就購置了兩支步槍和兩支轉輪手槍,同時向中國政府申領了持槍許可。據馬文·韋勒在《戈壁駝隊》一書里回憶,他們在甘南和臨夏交界處、蘭州阿干鎮附近、瓜州和敦煌地區都曾數次聽聞匪訊,甚至需要持槍戒備,所幸有驚無險,沒有發生開槍自衛的事件。
當年最令各路“驢友”聞之色變的,則是華家嶺上強人剪徑。
著名記者徐盈在其《西北旅行記》一書中有關于抗戰初期隴右匪患猖獗之描述:從寧夏到蘭州,本有一條直達的大路,但是這條路走起來實在艱難。抗戰初期,東北抗日義勇軍家屬前往新疆,從寧夏直奔蘭州,沿途居然遇到五股強盜,將其擊退后方能通過。“有些最厲害的強盜,不單劫物,而且還要殺人。”于是,當年旅客大多選擇前往平涼轉乘汽車赴蘭。然而,這條路線亦不平安,在將到蘭州之前,還要通過最后一重障礙,“這道丘陵地帶稱為車倒嶺,與祁家大山及華家嶺成為鼎足而三的難以通過的地方。都是除了路險以外,而且還是‘山大王’的出沒之所。”
那么,當年華家嶺上匪患有多嚴重?強人剪徑又是怎樣的場面?
《申報》記者陳庚雅在《西北視察記》一書里,曾詳細描述了自己于1934年冬乘坐長途班車(其實就是載客卡車)于華家嶺上“平生第一次遇盜”的經歷。
汽車駛上華家嶺,適逢雪天,銀裝素裹,陳庚雅一邊欣賞雪景,一邊贊嘆西北地區“樹掛”奇景:“舉凡一樹一草,皆以雪霧作用,宛似白銀鑄成,較彼平原雪樹,僅開梨花數點者,迥然不同。”正搖頭晃腦之際,忽聞“砰砰”兩聲,汽車戛然而停,眾乘客開始以為是爆胎,忽見車頭前四五步,有強人剪徑。根據陳庚雅記載,一眾強人分工明確,流程嫻熟。首先是兩匪持手槍立于車前作射擊狀,同時高呼:“快下快下!跟大家借些盤費!”待乘客跳下車后,另有三匪持杖,“令眾迅速排立,依次取遞銀物,匪一一接擲袋內,銀元互擊之聲,‘錚錚’作響不已。”與此同時,眾匪對于衣服闊綽者,“尚細捫之”。以陳庚雅為例,因其在西北旅行一年有余,風塵仆仆,穿著陳舊,且已將錢財及照相機等貴重物品打包進行李里,故而面對強人搜身,的確是囊中空空,“匪伸手探袋,誤日記簿為錢包,抓出一視,旋又遞還。”
然而就在此時,乘客中一名外國傳教士卻跳出來,面對一眾持槍強人,他聲稱不遠萬里到甘肅傳教亦屬替天行道,還請高抬貴手,日后也好相見,云云。眾匪面面相覷片刻后,盡管傳教士“喃喃哀求”,但“匪置諸不理,卒搜其銀”。
此次華家嶺剪徑事件的結局,還不算太壞,因為正當眾匪搜完身準備再搜行李時,恰遇甘肅禁煙委員會一輛貨車尾隨而至,押車士兵鳴槍示警,眾匪遂作鳥獸散。
撫今追昔,無論住宿、出行還是人身安全,甘肅的旅游環境較之當年有天壤之別。所謂人在囧途,往往是小概率事件抑或“驢友”們的自我調侃。但不管旅途囧事,還是人生挫折,昔日旅甘人士面對困難時的豁達心態仍然值得今人借鑒,正如陳庚雅華家嶺遇匪后之感言:“人生途程,本非平坦,事后回憶,亦覺有趣!”奔流新聞·蘭州晨報特約撰稿史勇
新化月報網報料熱線:886 2395@qq.com
最近更新
- 【天天新要聞】睡熱炕、走破路、遇盜匪...... 20世紀初游甘肅有多囧?2022-08-04
- 動態:現代人的臉為何比祖先小很多2022-08-04
- 時訊:靈臺公安局獨店派出所進農村開展交通安全宣傳2022-08-04
- 環球速遞!8月3日,甘肅新增無癥狀感染者11例2022-08-04
- 每日速讀!1年半跌了近200萬?“光明頂”龍光玖龍臺二手成交跌到6萬/㎡2022-08-04
- 天天頭條:熱帶低壓已登陸!深圳暴雨橙色預警生效!2022-08-04
- 環球最資訊丨公租房輪候排名19W能上車羅湖區公租房了!認租初審結果出爐2022-08-04
- 當前滾動:約500平方公里,深圳規劃“20+20”產業空間總體布局!2022-08-04
- 焦點熱門:東莞“保交樓”出新政!監管額度專款專用,開發商不得抽調2022-08-04
- 世界速看:車禍起火 “準消防員”抬手就滅2022-08-04
- 熱頭條丨問政快報(2022.08.04)2022-08-04
- 天天觀速訊丨樹新風一絲不茍 破舊習一寸不讓2022-08-04
- 環球資訊:「九江醫改工作系列報道之三」九江市推進醫療改革 有效緩解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2022-08-04
- 焦點熱議:南昌紅谷灘一托育中心承諾退費卻遲遲不落實2022-08-04
- 天天快報!“牽線搭橋”助力環保產業發展2022-08-04
- 實時焦點:貴州貴定:關愛職工到一線 高溫慰問送清涼2022-08-04
- 世界快資訊:公交站點無遮陽棚 上街沿又遭占道經營 乘客們等車犯了難2022-08-04
- 【環球新視野】南新鄉:統戰助力社會治理2022-08-04
- 通訊!7月銷量回暖,不是本田的最終訴求2022-08-04
- 焦點資訊:日本制造走向沒落?2022-08-04
- 天天熱消息:汽車元宇宙,距離我們還有多遠?2022-08-04
- 一險多用!福壽年年專屬商業養老保險搭建更穩固的“保障防護網”2022-08-04
- 榮威鯨安全配置拉滿,給你滿滿安全感2022-08-04
- 北京市臍血庫親子嘉年華|“臍”心一致,共赴美好未來2022-08-04
- 花牧軒生態茶餐廳:以原生態為主題 休閑娛樂餐飲理想之所2022-08-04
- 白家阿寬×肯德基推酸辣粉,這對CP組合絕了!2022-08-04
- 高培奶粉攜新品消博會首發 高培國際產業園助力自貿港發展2022-08-04
- 微念們投資建廠,我回到家鄉成為螺螄粉背后的打工人2022-08-04
- 百家IT廠商解答“時代之問”:數字化的下一站、增長方法論、未來3年布局點2022-08-04
- 在研究藍銅勝肽這條路上,為什么OGP能走在前面?2022-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