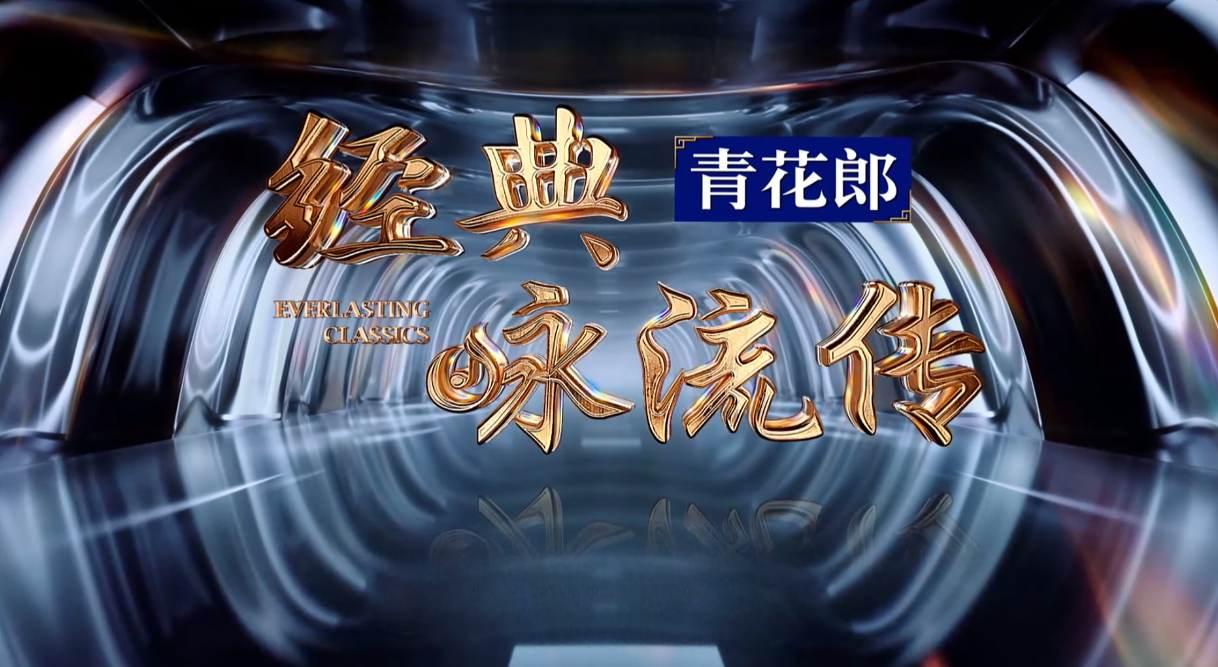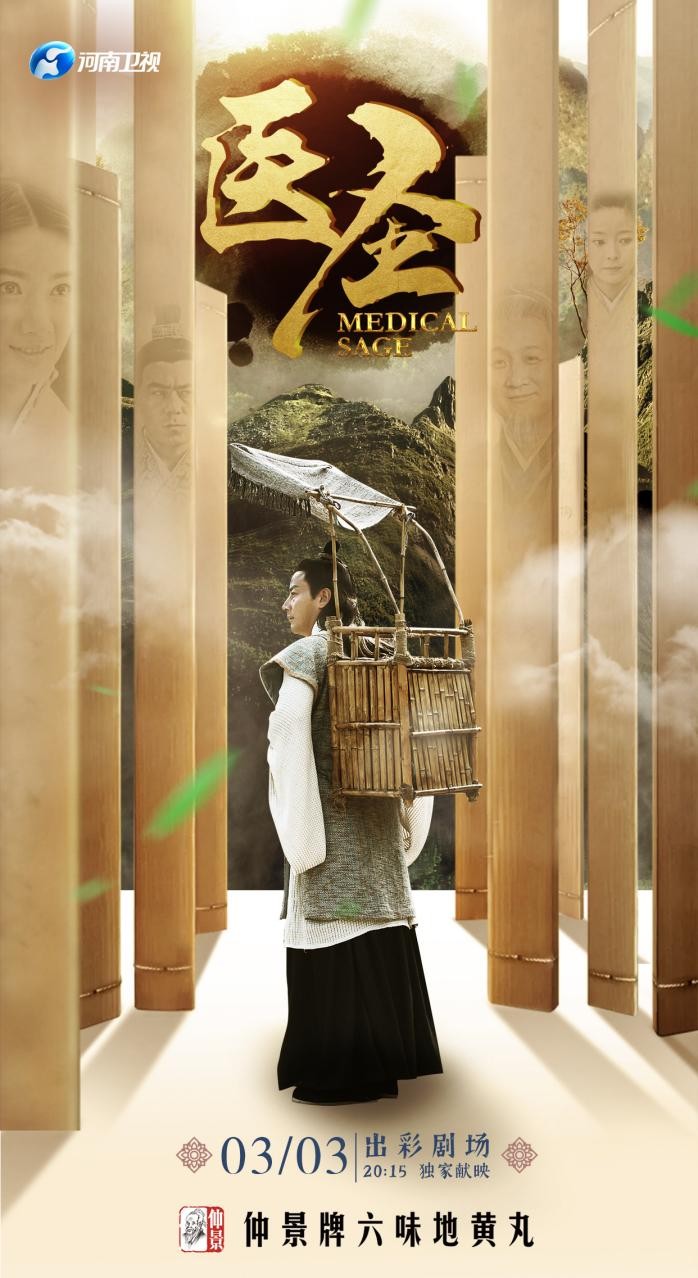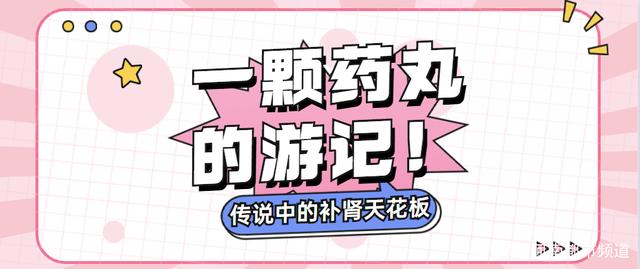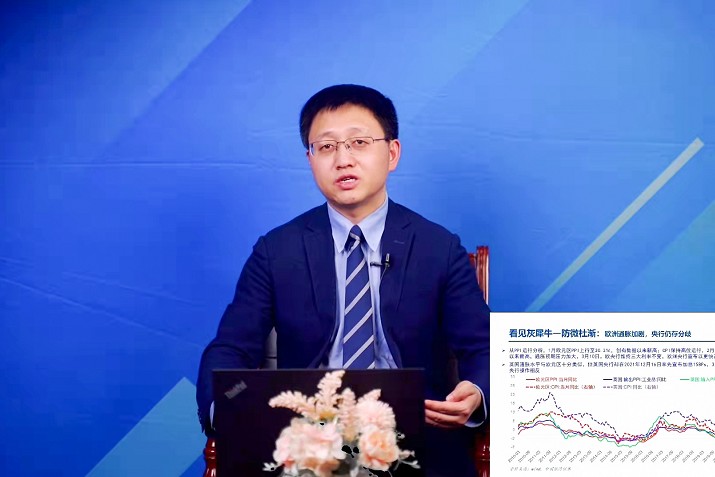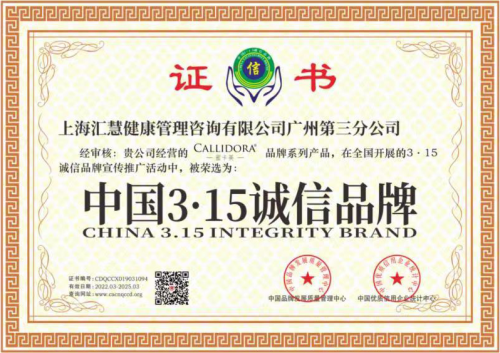在我家衣柜的抽屜里,存放著一雙黑褐色的尼龍襪子。十五、六年了,我還依舊不愿舍棄它。
這是一雙普通又便宜的襪子。唯獨不同的是,每只襪子的后跟都襯著薄布用細線一針針縫補過,針支均勻細密,穿上平順結實,幾乎看不出有啥破損的地方。它是母親那一年給我縫補的。
我三十多歲的時候,和妻子經過幾年擰緊腰帶的日子,終于在縣城置買了住房。有了新家,孩子也轉到城里上小學,而我們都還在三十里外的鄉鎮地方上班。母親已經七十多歲了,她說自己身體還硬朗,放心不下,就來照看孩子。我們白天不在,她要忙買菜做飯,還經常接送孩子,家里活硬是不讓我們操心。孩子去學校了,母親又閑不住,總要收拾屋子洗洗衣服。她不習慣用洗衣機,特別是娃的衣服天天用手洗。我們堅決不讓洗,卻總是攔不住她。晚上每回到家,常看到繩子上掛滿了晾曬的衣服。
有一天我回來,看見母親手里拿著針線,靜靜地坐在門口縫補著什么,再走近看,是我穿過的一雙舊襪子。我有些好奇,就問:“媽,你從哪里找到這的?”她仍是低頭一邊縫,一邊說白天收拾臟衣服,發現這襪子破了,就洗凈了來補。我有些埋怨:“媽,你不能歇歇吧?”她卻說:“這襪子只是腳后跟爛了,墊些布補補還能穿。”又遺憾地說:“可惜你們沒有縫紉機,要是放在農村家里,一會會就補好了。”我不解地說:“一雙舊襪子讓你這樣勞心,真不值得!”她釋然一口氣:“我看你們剛買了房,手頭緊巴巴的,再說襪子扔了可惜,覺得還是節儉些好。過日子就是這樣。”說完就不理我,繼續一針針的補起來。看著母親滿頭白發下戴著的老花鏡,專注的眼神盯著針線來回移動,我突然想起“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的詩句來,止不住眼圈發熱,一股眼淚流了出來。
母親不僅僅是在一雙襪子上這么節儉。她一生勤儉持家,憑著對生活的熱情和執著,在父親過世后,獨自奮力地養活我們長大,教育我們做人。
記得小時候在屋院前后,長著許多高大的槐樹、桐樹等木材樹,我們常常像在一把把碧綠的大遮陽傘下出入,處處涼爽舒快。遇到家里需要大的開支了,母親就合計著把哪棵樹伐倒賣了,過后再栽上新樹。她還栽植了石榴樹、杏樹、柿子樹等好多果樹,待到成熟季節,滿筐滿籠的果子吃不完,很多送給親戚鄰居分享。那時候不能隨便自由賣,市場上都在統一的供銷社買賣東西。現在回農村老家,眼前除了一排排整齊嶄新的平房外,各家門前也只栽些花草風景樹種,很少有綠蔭蔽戶的景象。人們吃水果,市場上到處都能買的,但我總覺得吃不出家產果的淳厚香甜味。
母親常在生活中適可教育我們做人做事。做飯的時候,我燒不旺火,她就放下案板上活,過來一邊用小鐵锨透空柴下的積灰,火苗就呼呼地冒起來,一邊還說:人心要實,火心要空。有時看我們買錯東西了浪費,就勸事先要考慮周到,說“吃不窮,穿不窮,計劃不到一世窮。”從她身上,我學到了許多書本上得不到的知識,讓我在以后的人生路上走的更加踏實穩重。
母親出身在舊社會一個條件較優裕的家庭,姊妹眾多,她是老大,很早就練就了農村婦女做飯裁衣的技巧本領。她做得一手好飯菜,簡單的食材也能調配得有滋有味。我記得她搟出的面條,齊整的跟現在機器壓的面分不出兩樣。村里來了公社干部、教師等公家人,村干部就常派到我家來。都知道她勤勞干凈,對人又熱情耐煩。那時候農村的孩子穿衣,主要靠手工縫制。母親常常連夜搖著紡車,一堆堆的棉花捻子都變成了細線。接著又進行漿、經、排等工序,最后才搭上織布機。
隨著我們生活條件慢慢轉好,工資收入也增加不少,穿衣戴帽都是買制成品。母親在世的時候,我們給她買一些適合老年人穿的時興衣服。她常高興地拿在手里,在身上不停地試劃,卻又問貴不貴,說城里花銷大,供孩子上學,以后不要再買了,自己在農村鎮上買。看著老母親始終這樣節儉,舍不得花兒子給她的一點孝順錢,真是長嘆一聲,天下父母總能體諒兒女,可我們能理會父母的多少苦心啊。
五年前,母親八十四歲高齡去世了,那是個酷冷的臘月季節。剛放寒假幾天,哥打電話說她病了。我回去還買了兩雙羊毛棉襪,到過年時她能穿上。真是“樹欲靜風不止,子欲養親不待”啊。風吹送著陣陣寒氣,晚上還下了一夜紛紛的大雪,早上母親帶著安詳永離我們去了。
這幾年我先后搬了幾次家,和母親一起生活的時間又不很長,有時候想起她,除看看她的遺照外,其他東西幾乎沒有了。只有這雙舊襪子,在整理衣柜時意外發現,我對妻子說不能丟掉,它上面留有母親勞作的手跡。每當拿起它,我就仿佛坐在母親的身邊,看著她戴著老花鏡,細心地一針一針密縫著……
作者:楊小牛
新化月報網報料熱線:886 2395@qq.com
最近更新
- 【清明憶故人·網絡寄哀思】一雙襪子的回憶2022-04-05
- 紹興越城區發現1例新冠肺炎初篩陽性感染者及“三區”范圍劃定2022-04-05
- 上海商家全力保障市民生活物資買得到、拿得到2022-04-05
- 三亞在全市范圍劃定封控區、管控區、防范區(詳見附表)2022-04-05
- 廣東加強柴油貨車環保監管 建立重點用車企業名錄2022-04-05
- 蘭州樓市調控放松:結清貸款按首套、二套3成、網簽3年可買賣2022-04-05
- 【清明憶故人·網絡寄哀思】清明憶亡妻詩三首2022-04-05
- 靖安縣高湖鎮政務服務暖心而有溫度2022-04-05
- 剛剛!福州閩侯再發重要通告!2022-04-05
- 鎮江市疫情防控2022年第21號通告(病例信息)2022-04-05
- 春城熱力:守護城市溫暖2022-04-05
- 廣州邊檢民警開展網絡紀念英烈活動2022-04-05
- 北京加強進京人員管控:抵京前或抵京后12小時內報備2022-04-05
- 守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新修訂的《甘肅省防震減災條例》解讀2022-04-05
- 人報甘頭條 | 蘭州新區44條出爐!力促服務業領域困難行業恢復發展2022-04-05
- 千年壁畫“動”起來了 敦煌歲時節令之清明篇2022-04-05
- 【網絡中國節·清明】蘭州開展“2022·奮進·網上祭英烈”紀念活動2022-04-05
- 【視頻】春光正好賞杏花2022-04-05
- 快自查!B類密接人員行程涉及涇河新城轄區 具體風險點位公布2022-04-05
- 守護“菜籃子”“米袋子” 太原公安交警保障運輸線暢通2022-04-05
- 英烈“歸隊”!江西于都舉行零散烈士墓集中遷葬入園儀式2022-04-05
- 中山沙溪鎮一物流園臨時管控2022-04-05
- 22地出臺十四五裝機規劃 風光新增裝機規劃總規模已達558.6GW以上2022-04-05
- 曾主導大眾CC的設計師Martin Kropp:AMOLED屏帶你體驗飛凡R7的別樣精彩2022-04-05
- 北京疾控:乘高鐵返京病例在京外候車期間感染可能性較大2022-04-05
- 剛剛通報,濟南這些場所實行“全封閉”2022-04-05
- 淮南通報:公安機關依法對初篩陽性的衛生院員工李某龍立案調查2022-04-05
- 北京本土確診+1,服裝店關聯傳播鏈再延長!涉這些時間和點位的人員請報備2022-04-05
- 【網絡中國節·清明】清明來自云端的思念 蘭州市龍鳳園公墓全園代祭緬懷逝者2022-04-05
- 國網沈陽供電公司:幫無法返家用戶“停電”2022-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