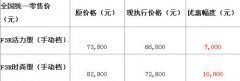|
采訪組:您提到,習近平曾對常振明說:“你們那個孔丹,窯洞里還讀黑格爾呢!”您能講講這件事的由來嗎?
孔丹:那時我是中信的董事長,常振明是總經理。有一次,他去上海見到了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他回來告訴我:“我見到習書記了,習書記對我說,‘你們那個孔丹,窯洞里還讀黑格爾呢!’”
我和習近平當年在陜北沒見過面,但互相都有耳聞。這一則因為我們當時在知青里都是有名的“黑幫子弟”,或許也都小有名氣吧。二則因為我們的父輩是相互熟悉了解的。2009年,習近平到河南洛陽調研時,視察了他父親習仲勛落難時下放勞動過的洛陽礦山機械廠,這個工廠改革開放以后成為中信的重機公司,所以我前往接待。一見面,他就對周圍同志說,孔丹的母親和我父親在國務院是同事。我趕忙應答,哪里是同事,習仲勛同志是副總理兼秘書長,我母親只是副秘書長,是下級。他笑言,那也是同事啊。
插隊期間,勞動是艱苦的,生活是艱難的,好在政治上還是平穩的,書還是可以讀的,讀書的時間也是有的。傍晚下工后,吃完了飯,剩下就是自己安排了。特別是冬天除了一些水利工程類的活兒,基本上沒有太多地里的活兒了,如果不回北京,就有時間好好看點書了。我后來了解到,習近平當年讀的書很多,主要是政治、經濟和文學類書籍。我讀得書很雜,但凡能找到的書都讀,大多是從北京帶來的書。因為中學的全部課程我在四中時已經學完了,就找來大學的高等數學、普通物理、普通化學教材學習,這些都是大學理工科一二年級的公共課教材。當時比較寶貴的內部出版的書,像《托洛茨基評傳》、德熱拉斯的《新階級》等政治類的書,還有中國古典文學、外國古典文學等等,都是那時候讀的。習近平當年帶去兩箱子書,讀完之后又不斷交換,借書來讀,再加上他在一些講話中提到的讀過的作品、引用的作品,我感覺他讀書的數量和種類超出了我的閱讀數量和閱讀種類。
我那時候讀書,并不是像有些革命家那樣有遠大理想,什么去改造社會、改造國家,沒有。只是覺得讀書是我們一種天然需要。我們在土窯洞,自己打了一個石板,把兩個樹干插進土窯洞,再來一個橫的樹干,把石板鋪上,就可以趴在上面讀書了。現在回憶起來,陜北的黑夜就像一幅永恒的影像,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陜北的天似乎黑得特別早,可能是因為在山里吧。夏天還好一些,秋冬黑得尤其早。天黑得早也好黑得晚也好,冬天也好夏天也好,我們幾個人往窯洞里一坐,大家把各自的書拿出來就開始讀。黑夜中伸手不見五指,只有窯洞里有一盞煤油燈,閃耀著一絲亮光。我們湊著那個煤油燈,趴在石板上看書。我后來了解到,習近平當年在窯洞里晚上讀書,也是湊在煤油燈前,以至鼻孔常常都被熏黑了。
那時對我們來說,讀書是一種享受,打開書本馬上就可以進入另外一個世界,一下子就和現實生活隔離了。你不會再想白天干什么活兒了,不會再想白天的疲憊和困倦,你會鉆到書里面去。看哲學書、文學書、歷史書,你會被它們吸引,馬上進入另外一個不同的境界。在《戰爭與和平》中,可以看到在拿破侖戰爭的宏大背景下俄羅斯貴族的生活,可以看到戰爭的滾滾硝煙;在《九三年》中,可以看到法國階級斗爭激烈而雄偉的場面,可以看到革命紀律的堅強意志與私人感情的艱難抉擇。正如習近平所說,在陜北插隊時我確實讀了黑格爾。讀沒讀過黑格爾是不一樣的,受沒受過熏陶和訓練的思維是不一樣的。后來有人說,如果一件事情在邏輯上不完整或者不自洽的話,孔丹是不會接受的。其實,這里面就是理論的力量。1977年恢復高考,我沒有報考大學,而是于1978年直接報考了中國社科院經濟專業的研究生并被錄取,成為恢復研究生招生制度后沒有上過任何大學、以同等學力考取的第一屆研究生。能有這樣的結果,除了在北京四中打下的扎實基礎外,與陜北插隊時堅持讀書學習是絕對分不開的。
那時,劉少奇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對我影響很大。我還受很強的儒家思想的影響,儒家思想強調“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不記得從哪里弄來一本講美國農業生產方式的書,介紹他們采取的集約式生產方式,效率很高。我國農村經歷了1958年“大躍進”,1962年人民公社體制改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開始下放所有權,應該說已經沒有了原來吃公共食堂那種大鍋飯的現象了。但在我們那里,一個大隊里邊還是一起出工、一起收工,干多干少一個樣,勞動生產力極其低下,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大鍋飯。看了講美國農業生產方式那本書,我就想怎么發展中國的農業。這種想法當然是初級的、幼稚的。后來,中央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時,我就覺得是自然而然的事,特別容易接受。但在黨內就引起一些爭論,包括一些省委書記都對此事有看法,認為應當避免集體生產方式被破壞。而對我來說,因為有四年插隊生活的經歷,又讀過農業研究方面的書,我就覺得這件事很容易理解,是大勢所趨。我始終認為農民的積極性是天然的力量。當然,今天發生了很多新的變化,我們要重新研究怎么解決土地流轉問題,怎么調動農民積極性問題,以及兩億七千萬農民進城后誰來種地和種好地的問題。要解決好“三農”問題,必須基于對農村和農民的深刻認識和理解。
采訪組:習近平總書記曾說,“要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您怎么理解?
孔丹:我個人理解,就是要養成良好的學習和閱讀習慣,樹立自己的正確人生觀,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對于我們那一代人來說,可以說插隊就是我們“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因為我們要自己面對社會,社會已不再把我們看成少不更事的孩子,而是把我們當成一個成人來看待。陜北老鄉都是善良的,他們沒有因為我們是“黑幫子弟”而另眼相看。我記得有一位老大娘,她知道我家里的遭遇,對我特別關心。有一次,我把被子拆洗了,剛晾干,老大娘就拿著針線過來給我縫上了,她一直把我當成半個兒子看待。
我走山路的能力就是在那個時候練出來的。陜北都是高高低低的山路,每天一出門就開始爬坡、下坡。老鄉告訴我,走山路可急不得,得走得慢慢的、穩穩的,才能走得遠。要是心急,一會兒就能走出一身汗,還能叫你喘半天!老百姓中間蘊藏著大智慧,走山路如此,做人做事何嘗不是如此。越是遇到困難,越不能著急,一定要慢下來,穩下來,才能克服困難,走得更遠。“行穩致遠”,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老鄉對我們很熱情。當地老鄉都是抽煙袋,剛到農村時,有位老鄉抽完一鍋煙后,就把煙嘴在衣服上一蹭,再用煙絲裝滿煙鍋,遞給我抽。一開始我還真不習慣,可是又不能拒絕老鄉的盛情啊!我只好硬塞在嘴里,老鄉見我和他們一樣抽煙,就覺得跟我親近,還高高興興幫我把煙給點上。我記得很清楚,當時第一口煙就“暈煙”了。那煙太厲害了,就像在嘴巴里面炸了似的,鉆到我的鼻腔里、肺里,嗆得我直流淚。看著老鄉真誠熱情的眼神,我硬是挺著沒咳嗽出來。從那以后,我就跟著老鄉一起抽煙了。我一直抽了34年的煙,直到2003年“非典”才戒了。僅僅從抽煙這一件事來看,陜北老鄉和農村對我的影響可謂至深,或者叫“深入骨髓”。
還有一件涉及抽煙的小事,讓我至今難忘。為了抽煙,我跟別人打賭,說我一口氣能喝半斤酒。別人不信,我們就走了五里多路,到公社的供銷社用洋瓷缸打了半斤酒,我當場端起來一口氣喝光了。那人當即就服了,輸給我3條煙。當時一條煙6毛錢,6分錢一包的經濟煙。這件事既顯示了我的男子漢本色,又贏了3條煙,讓我開心了很長時間。直到今天,回憶起這件事仍讓我忍俊不禁。這就是陜北農村帶給我的快樂,這種快樂就像一枚寶石珍藏在我的記憶中。每每想到這些快樂的事情,陜北的農村、陜北的老鄉就浮現在我的眼前。那片土地不僅僅是我勞作過的土地,而且是我靈魂的故鄉;那里的老鄉不僅僅是陪伴我的老鄉,而且是我精神的手足。我覺得我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扣好了。
到陜北插隊同樣是習近平的人生第一站。當年他年紀那么小,在黃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而且扎扎實實干成了那么多很不容易干成的事。所以說他的人生第一站走得更扎實,他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扣得更好。這也是他以后走好人生其他旅程、系好人生其他粒扣子的最重要基礎。
|

 手機版
手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