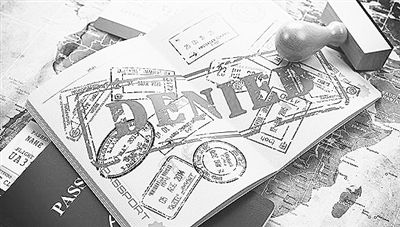
圖片來自網絡
最近西方世界彌漫不散的政治動蕩,讓科學孤立主義、不熱衷合作、流動性減弱等趨勢抬頭。
上個月,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發布了一年之內的第三次旅行禁令,不允許特定國家的人進入美國,還對更多類型的簽證進行限制。這些命令阻礙了滯留海外的學者和在國內從事國際工作的人的自由流動。
再往前看,3月份,英國首相特里薩·梅開始正式切斷與歐盟的關系。英國機構面臨非駐歐盟科研人員的潛在流失局面,還將花力氣破除藩籬,以順暢地參與歐洲聯合科研項目并獲得資金支持。
日前,《自然》官網刊登了一份詳細的研究報告,以更好的方法衡量科研人員的流動性,進而評估這些政治行為的影響。
樣本量浩大的細致“摸排”
印第安納大學情報學與信息學院副教授卡西迪·R·杉本課題組發布的這份報告,基于對科研人員全球流動性的分析,試圖揭示科學體系受到的影響。
雖然科學人才的規模和組成通過國家調查和注冊機構已經十分成熟,但了解科研人員的流動頻率、他們去了哪里、形成了哪些網絡,以及其流動對科學工作的影響非常重要。
課題組的分析數據來自于2008年至2015年間1600萬名獨立科學家發表的1400萬篇論文。其中,96%的科研人員只有一個國籍,他們屬于非流動人員。大約4%(超過59.5萬名科研人員)是流動人員,他們在這段時間內有服務于多個國家科研機構的經歷。結果顯示出驚人的趨勢:歐洲和亞洲的科研人員流失嚴重,而北美入境科研人員則大幅增加。
“大腦流通”影響力不容小覷
此前有假設認為,歐亞流出科研人員以犧牲原國籍為代價,換得了流入國的科學資本。但現實更復雜。
課題組發現,大多數科學家沒有減少與原籍國家的聯系,而是建立起了一個將各國聯系起來的學術網絡。許多人還回到了祖國。
“大腦流通”似乎更適合描述這類人。研究發現,無論他們在哪個國家,或者駐留在哪里,他們的論文引用率,都比非流動科研人員的論文引用率高出40%。
在流動科研人員中,有不到三分之一(占所有流動人員27.3%,即162519人)屬于傳統的移民科研人員,他們首先在一個國家發表了文章,然后轉移到另一個國家繼續科研工作,在某種程度上停止了對前一個國家的依附。另外三分之二(72.7%,即433375人)的流動科研人員,在整個科研生涯中始終保持與自己祖國的聯系,同時還收獲了更多的國際關系。
通過繪制科研人員數量和流量的流通網絡,研究發現,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和德國是全球科學網絡中最集中的節點。對這些國家的隔離政策,將產生巨大后果。
亞洲和北美洲之間流動頻繁
接著,研究團隊將樣本范圍縮小,集中在那些于2008年發表了第一篇文章,且在2015年之前至少發表8篇文章的人身上。這意味著只專注于研究初級學者,這樣避免了與資深科學家的混合,因為后者的流動軌跡和網絡會與目標樣本有所差別。
在鎖定的12046名研究人員中,歐洲占據最大比例,達到了35%,其次是亞洲和北美地區,占到了25%。亞洲和北美之間的關系比較強大,2008年第一次發表論文的亞洲國籍流動科研人員,多數在2015年發表論文時標注了北美洲的地址,而同時北美洲的流動科研人員中也有三分之一在亞洲。這兩個趨勢可以解釋為相同的現象——亞洲學生涌入美國,隨后回歸亞洲。
數據顯示,歐洲科研人員流失22%,亞洲流失20%,而北美地區卻收獲50%。歐洲科研人員幾乎在每一個國家的流動人數中占到了最大比例。
高影響力來自少數流動人員
了解一國對高影響力學者的培育和負責程度也很有意義。課題組通過查看流動科研人員在流動前后的文章引用指數來評估這一點。
北美和北歐國家作為強大的科研人員生產者,他們對人才的投入和培育以及發掘,都關系到其后續的科研影響力。亞洲是人才納入的強大地區,收獲了很多知名科學家。而大洋洲是值得注意的孵化器,能夠培育出高潛力的科研人員。
在所有地區,流動科研人員比非流動人員更引人注目,但地區不同,優勢各異:高影響力的北歐人被招募到南歐;高影響力的西歐人則被招募到大洋洲和東亞;來自大洋洲的流動科研人員到達北美和南歐時,會獲得高影響力的工作;中西亞(包括美國禁止入境的國家)科研人員在北美和歐洲的工作成果獲得了最高的引用率。
總而言之,研究團隊認為,在流動性、復雜性日益增加的時代,科學勞動力的國際可比流動指標尤為重要,這些指標能為人力資本和知識經濟的交流提供更細致和更有針對性的評估。
事實證明,國際流動科研人員雖然占少數,但影響力巨大,限制其流動性可能對越來越依賴國際合作的科學體系產生不利影響。
新化月報網報料熱線:886 2395@qq.com
最近更新
- 全省法院實現訴訟費繳退費“線上辦” 傳統線下繳退費功能為何仍保留?2022-01-15
- 受疫情影響西安部分區縣蔬菜滯銷,亟需各方助力解決2022-01-15
- 恩施州6個重大交通運輸項目集中開工!總投資32億元2022-01-15
- 【15號用】3崗招聘若干人!45歲以下可報!五險一金+包食宿!2022-01-15
- 國際科技合作助推湖南優勢領域提升國際競爭力2022-01-15
- 延安城區新增車位3100個 有效破解停車難2022-01-15
- 鴻星爾克入選2021年“誠信之星”!2022-01-15
- 菏澤農商行新興支行開展包片行政村信貸產品推介活動2022-01-15
- 鞏義市:黨員“雙報到”進社區 為民服務“不打烊”2022-01-15
- 廣東珠海1月15日新報告1例本土確診病例2022-01-15
- 大降價!阜陽即將啟動2022-01-15
- 北京專報丨國家衛健委:天津疫情仍在持續發展,西安疫情進入收尾階段2022-01-15
- 陜西對符合解除隔離條件人員 落實后續7天居家健康監測措施2022-01-15
- 信陽消防聯合多部門 開展應急實戰演練2022-01-15
- 城西區:“紅色存折”讓社區志愿服務更有溫度2022-01-15
- 乘動車忘帶身份證 可開電子證明2022-01-15
- 陜西組建2400人的省級醫療團隊 支援本土確診病例救治工作2022-01-15
- “德爾塔”與“奧密克戎”,救治有何不同?2022-01-15
- 手拉手共成長 長沙清水塘北辰小學孩子“牽手”湘西娃2022-01-15
- 抓整改 提標準 縣住建局全力提升城市精細化管理水平2022-01-15
- 破防了!這家山東科技企業的暖心行動2022-01-15
- 臨潼區:多措并舉助力農業復工復產2022-01-15
- “這個嘉賓思路厲害”,市消保委委員張兆安做客《海波熱線》特別節目2022-01-15
- 福州市副市長、公安局長王錫章帶隊到莆田市公安局考察調研疫情防控工作2022-01-15
- 合肥這家知名書店,新年再出發2022-01-15
- 崔同富到武定縣開展春節走訪慰問2022-01-15
- 北京:迎接冬奧會和冬殘奧會長安街開始布置花壇2022-01-15
- 洋碼頭首家文旅免稅直購店落地重慶十八梯景區2022-01-15
- 每戶將分到70斤!更多物資送達……直擊杭州西溪雅苑封控現場2022-01-15
- 本土確診+104,其中河南+52,天津+39,珠海新增感染者均系奧密克戎2022-01-15























